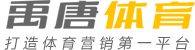当洋巨头反攻,安踏与耐克们为何踩下急刹车?
某种程度上,世界运动鞋服产业史就是耐克与阿迪达斯的竞争史。
在全球经济遭受多重挑战的大背景下,运动品牌圈却出现了罕见“温差”。
近日,阿迪达斯(adidas)公布了其第三季度初步业绩,并上调了全年的业绩预期。
报告期内,毛利率达51.8%,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3%至7.36亿欧元,推动公司今年前九个月的营业利润率上升至10.1%,高于首席执行官Bjorn Gulden比约恩·古尔登年初设定的目标。
据财报显示,在全市场、全品类、全渠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推动下,阿迪达斯品牌全球营收达66亿欧元,创下公司有史以来单季营收最高纪录。由于去年年底完成了剩余Yeezy库存的销售,本季度业绩未包含任何Yeezy库存销售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华区交出连续第10个季度正增长,Q3营收同比再涨12%,全年有望突破35亿欧元,创2019年以来新高。
对于阿迪达斯来说,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因为从2021年二季度到2023年一季度,阿迪达斯大中华区业绩连续8个季度营收下滑。
不过,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近日,雪中飞代工阿迪达斯羽绒服这一事件登上热搜。
“我不如直接买雪中飞,中间的差价是买logo嘛?”几天前,北京一名消费者吐槽称。
经对比,该款阿迪羽绒服绒子含量80%、蓬松度600+,而雪中飞相似款羽绒服绒子含量达90%、蓬松度680+,价格还低60元。此事引起大众对阿迪等大牌溢价产品的广泛议论。
在舆论持续发酵后,阿迪达斯官方客服回复称,雪中飞、波司登都是阿迪达斯羽绒服的代工厂。将这一事实再次推到台前:阿迪达斯这家全球运动品牌巨头,几乎没有自己的生产线。
事实上,阿迪达斯很早之前就将品牌和制造环节进行了分离,基本不再自建工厂,主要靠代工厂完成其产品的生产制造。只有少部分专业运动装备或在德国本地生产的高端系列由阿迪达斯自己生产,但占比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运动鞋服行业的代工模式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一线品牌,在中国都没有自己的工厂,全部委托第三方工厂生产:2009年耐克关闭了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阿迪达斯则在2012年关闭了在华唯一直属工厂。
据了解,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超过80%由本土工厂生产,从纱线、面料到成衣平均交货期仅21天,比越南工厂缩短一半。
而且,每个品类都由不同地方的工厂代工,比如鞋类代工厂高度集中在广东、福建等地,如万邦鞋业深耕阿迪达斯Originals经典系列,荣诚集团则侧重生产高尔夫球鞋、登山鞋等专业功能鞋款。针织服装制造商申洲国际则与阿迪达斯采取纵向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从面料研发、织造到成衣全程都负责。
这次引发关注的雪中飞,专门为阿迪达斯代工羽绒服产品。天眼查显示,江苏雪中飞制衣有限公司由江苏康博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后者为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实成为阿迪达斯的代工厂并非易事,品牌方对代工要求极高,验厂、验货等环节的烦琐与细密近乎苛刻。
据了解,为阿迪达斯这类国际大品牌代工的企业,不会主动披露其合作关系,这背后是由商业规则、法律合同与品牌战略共同约束的。
品牌方与代工厂签订的合同中,会包含严格的保密条款。这些条款明确禁止代工厂未经许可使用品牌方的名称、商标进行宣传,或公开披露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违反这些条款可能导致高额赔偿甚至终止合作。
2025年4月,美国掀起的关税战,让尝到战略回调甜头的阿迪达斯,加快了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当许多国际品牌仍在权衡“是否加码中国”而犹豫不决时,阿迪达斯的选择早已清晰:这里的增长,不是偶然的红利,而是本土化战略结出的必然果实。
内忧外患,继续下沉
时间回到2023年,当时的阿迪达斯还身处内忧外患中:内部策略失误,如产品创新乏力、品牌定位模糊、对市场反应迟缓;外部环境巨变,如国产品牌崛起、宏观环境出现调整。这导致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收入,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下滑,这种颓势一直持续到2023年第一季度。
这一年3月,时任CEO卡斯帕·罗思德提前离职,他曾公开承认“在中国犯了错误”。新任CEO比约恩·古尔登上任后,从渠道、产品、品牌营销等方面做出不少调整。除了以本土化战略为核心外,灵活下沉、转向潮流作为改革的两翼同步进行。
在渠道上,阿迪提出携手合作伙伴在“未来市场”积极开设新店。其一边在一二线城市关闭效益不佳的店铺,一边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加大布局,借助经销商网络,加速进入下沉市场。
在产品上,用Samba系列开路,让失去Yeezy后的阿迪达斯“触底反弹”,并斩获“2023年年度鞋款”,其定价维持在1000元以下,促销折扣下,部分款式可达300-600元一双,平替版本VL COURT系列更是进一步将价格拉低至200-500元区间,把“濒死状态”的阿迪达斯拉了回来。
该鞋款不仅频繁出现在全球明星、网红博主、球鞋爱好者的穿搭LOOK中,在超模肯豆、说唱歌手Pusha T、演员马思纯等名人的带动下,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此外,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萧家乐在2026春夏上海时装周打出“诞生于赛场,闪耀于秀场,风靡于街头”的口号,三叶草限时空间3天吸引2.4万人次打卡,小红书相关笔记浏览量破1.2亿;品牌代言人李现同款卫衣48小时全网断货。
通过“运动+潮流+明星”三板斧,阿迪达斯2025年Q3在18-25岁人群中的品牌偏好度回升至32%,较2023年低谷提高9个百分点,首次反超耐克(30%)。
其实,某种程度上,世界运动鞋服产业史就是耐克与阿迪达斯的竞争史。
“大人们”今时不同往日
在耐克崛起之前,全球运动鞋服呈现德、美、日三足鼎立的局面。包括以阿迪达斯、PUMA为代表的德国品牌,以New Balance、匡威等为代表的美国品牌,和以鬼冢虎为代表的日本品牌。
耐克的突起,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1980年,耐克在北美份额第一次超过阿迪达斯,达到50%。
同期,阿迪达斯因运动时尚风潮推进滞后而低迷,90年代起高度重视并持续发力运动时尚潮,并1996年推出Originals复古系列,从而拉动品牌复苏。1994年起,阿迪持续保持20%以上增速。再加1998 年收购萨洛蒙品牌,收入规模再上台阶。自此正式进入耐克与阿迪达斯双雄争霸的行业格局。
回到中国市场,亦是类似态势。
在很长时间范围内,都是耐克与阿迪达斯之争。但在2017年以来,安踏、李宁、FILA等品牌快速崛起,阿迪达斯跌势尤其明显。在2024年,阿迪达斯在华市场占有率已经低于耐克、安踏与李宁。
日前,安踏集团发布今年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其中安踏品牌和FILA品牌的零售额(线上+线下)同比录得低单位数正增长,可隆、迪桑特等组成的“所有其他品牌”同比增长45%至50%。今年新收购的德国狼爪品牌,其业绩暂未披露。
放眼行业,耐克的日子也不好过。据其公布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对应自然年2025年6月1日至8月31日)显示,全球市场实现营收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1%,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市场均实现正增长,扭转了去年以来的颓势。
但大中华区营收仍在新财季下降10%至15.12亿美元。这与耐克前任CEO推行的DTC转变导致企业与经销商关系紧张有关。滔搏作为耐克最大的中国经销商,2025财年(2024年3月-2025年2月)营收270.1亿元,下滑6.6%,净利12.9亿元,跌幅达到41.9%。
现任CEO贺雁峰(Elliott Hill)上任后聚焦专业运动,主导修复经销商关系、出清旧款式,2025财年在华库存已经同比下降11%。但营收增速转正仍需时日。
事实上,国内运动市场正在遭遇增长压力。
此前,匹克董事长许景南在内部会议上提到,匹克内销直营板块自年初以来持续亏损,仅1月至7月就累计亏损逾1.3亿元,期间还不得不转手三个分公司。由此,匹克选择实行阶梯式降薪,最高降幅达50%。
在如此环境下,在阿迪达斯的“高调”进击中,其他运动品牌的对策显然是大力应战。当然,在国内市场,他们都面临着国产品牌崛起的现实压力。
尽管已在大中华区取得连续约十个季度的业绩增长,但阿迪仍未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并与竞争对手存在一定的差距。
据欧睿数据显示,阿迪2021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有15%,到2024年已跌至8.7%,低于同期耐克的16.2%、安踏的10.5%与李宁的9.4%。
在中国市场,品牌胜负从来不是“国货”与“洋货”的身份之争,而是“谁更懂中国消费者”的能力之争。
当阿迪达斯用80%本土制造把交货期砍到21天、用上海时装周+李现把Z世代重新拉回三叶草门店,它已经完成从“外来者”到“在地赢家”的身份切换。
反观安踏与耐克,一个被“高端化”反噬,一个被“创新断档”拖累,共同陷入库存与价格的双杀。
运动服饰江湖的残酷法则再次应验:没有永远的国货红利,也没有永远的海外魔咒,只有“供应链速度+科技锚点+情绪价值”三要素同时在线,才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运动消费市场站稳脚跟。
下一个季度,阿迪达斯的增长曲线是否会继续向上?答案尚未写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永远只为“懂我”的品牌停留。
本文转载自NewSportsGo,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当洋巨头反攻,安踏与耐克们为何踩下急刹车?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禹唐体育原创文章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