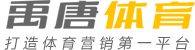北京滑冰往事
冰场主要开早晚两场,早场人少,夜场却场场爆满,尤其最热闹的什刹海冰场,每天都有因抢不到票悻悻而归的人。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有两面带名字的“墙”,一面属于冬奥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男子速滑项目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高亭宇赫然在列,另一面属于10名普通的滑冰爱好者,他们代表男女老少创造的“市民纪录”,和挑战人类极限的“冬奥纪录”一起,成为这座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的一部分。
竖起两面墙,间隔近一年,这一年恰是“双奥之城”北京进入后冬奥时代的开始。
“上道、发令、起跑、比完了播报成绩,包括赛后回放,跟我看冬奥会一模一样。”速滑发烧友小石参加了首场“冰丝带”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虽是群众赛事,但比赛使用了速度滑冰专业电计时系统完成现场成绩实时处理,采用4个转播机位的现场转播上屏和线上直播,“场馆冬奥标识还在,滑的时候感觉真跟自己参加冬奥会一样,有点儿穿越的感觉。”
在如同镜面的冰面上贴地飞行,速度感与失重感确能营造错觉,对于老年组56-65岁男子500米冠军宫延利来说,刚过去的54秒66,像是把时间撕开了道口子,一股脑儿涌出的是近50年的滑冰往事。
自织毛线裤和“靡靡之音”
“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北京滑冰最火的时候,随便开个冰场,买票基本都得排队。”宫延利是60后,在他的少年时代,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滑冰潮留下的“老冰场”成了当时年轻人的聚集地,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龙潭公园、玉渊潭公园、颐和园昆明湖甚至护城河等冰面上,被一代代年轻人用冰刀划下青春的印迹。
冰场主要开早晚两场,早场人少,夜场却场场爆满,尤其最热闹的什刹海冰场,每天都有因抢不到票悻悻而归的人。宫延利就曾“跑空”过,“大概晚上5点半开场,我4点多到,一直排队,轮到我已经没票了。”
“什刹海冰场是北京的一个中心冰场,当时一到周末,滑冰爱好者全到这儿去了,技术切磋,用现在的话说叫‘PK’。”年届七旬的崔克岭比宫延利上冰更早,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冶钢厂工作,冬天看厂里岁数大的人滑冰“挺新颖”,从此找到了坚持一生的爱好。可工厂位于昌平,离城区有40公里,想回城滑冰得先坐火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再转公交车坐到北海,紧赶慢赶,到冰场6点半,能滑到8点,花两毛五分钱在灯光、音响中享受一个飞驰的夜晚,“就这么一直坚持着”。
坚持了几十年,崔克岭和冰友成立了什刹海速滑俱乐部,他们有整齐划一的服装和冰鞋,鲜红的速滑连体服上,大腿位置黄色的“什刹海”3个字非常抢眼。可当年,冰场上最时髦的穿着是军大衣和羊剪绒军帽,“衣服得敞着穿,要是军大氅就更了不得了。”崔克岭当年有一顶“拿得出手”的帽子,尽管媳妇儿总叨叨“占地儿”,但他始终没舍得扔,可军大氅很难指望,拼技术的冰友就向运动员看齐,“一套绒衣绒裤,条件好的就织个毛裤。”
为了织条毛线裤,何广深拆了很多家里的毛线手套,然后花几分钱买包颜料染色,“那会儿夜场大概零下一二十摄氏度,大家都先穿着棉裤运动,热身差不多了,棉裤一脱,自己动手做的黑色毛裤就能派上用场,赶紧臭美一会儿。”打年轻时,何广深就要做“冰场上最靓的仔”,如今,68岁的他留着银发低马尾,黑色速滑服配万元的顶级冰刀,加上滑行的绝对实力,早已成为圈里公认的“何大侠”。
在他记忆里,小时候用哥哥的鞋接触过滑冰,可直到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第一双冰鞋,才开始正式练习滑冰,“1973年,天津的鞋,双层皮子比较贵,配黑龙的刀,一套将近40元。”尽管,当时的刀滑一会儿会弯,“得拿膝盖顶顶”,但一个月工资奢侈换来的是至今都能嚼出甜味儿的时光,“下了班好兴奋,饿着肚子就骑车赶去滑冰,滑完回家吃一口剩饭,特幸福”。
偶尔也有经不住饿的时候。溜冰场的大暖棚是冰友的“续航站”,柳条编成席子,用铁丝固定围成一圈,中间生火,供大家取暖,还有各种小吃,炸豆泡儿一度让何广深眼馋,“不敢吃,太奢侈了,滑一场冰就好贵”。
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溜冰场的一切都是梦幻的,从各个工厂涌入的青年男女、点亮黑夜的灯光、喇叭里悠扬的《溜冰圆舞曲》,这里能暂存无处安放的青春,也能窥见外面的世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冰场上出现了一些“南方传来的东西”,例如,喇叭裤等“奇装异服”以及手提录音机里传来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没过多久,“奇装异服”成了大众潮流,“靡靡之音”也成了“流行歌曲”,崔克岭感受到,改革开放真的来了。
时代浪潮下的聚散
在通讯不便的年代,北京的冰友却有着高度默契。周末什刹海的切磋,到了大年初二就转战颐和园,不同冰场的代表分成几拨亮出绝活儿“茬冰”。
但在崔克岭记忆中,最不需要商量的就是每年冬天上冰,“我们是一年见一季的朋友。”他表示,即便没有电话、微信,但只要过了节气,大家见面的日子也就近了,“小寒一过,就开始观察冰,先是家里往道儿上泼水,看会不会结冰,然后去水面观察,今儿一看封半截儿了,明儿再来看,哟,都封上了。”这时,水边就能遇到熟人,“纷纷背着鞋来了”。
为了避免跑冤枉道,冰友想尽办法测冰,看不准冰的厚薄,就拿着砖头一扔,“咕噜噜噜”一响,代表“有希望了”,再到边上用砖头凿下一块冰,一捏,崔克岭先用三根手指比了大约5厘米,相当于一本新华字典的厚度,“这么厚不行。”然后,他把手指间距拉出3本字典的厚度,“这么厚,行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来测冰的人减少了,宫延利发现,冰场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机会,单干、下海、各奔东西了。”滑冰的热潮似乎被更大的时代浪潮吞噬了,宫延利成了为数不多浮在水面的人。
再往后10年,随着市场规范和社会安全意识的提升,冰友能选择的冰场和公开水域越来越少,“尤其喜欢速滑的,找不到合适的场地,人数急剧下降,一批人选择小冰场,改滑短道速滑了。”宫延利没有改项,像打游击一样,在首体速滑馆、陶然亭冰场和没人管的河道里“自己玩玩”,“中午暖和,自己背着鞋去‘呼呼’滑20分钟,中间冷不丁还能叫几个朋友,再后来就叫不到人了”。
在宫延利踽踽独行的日子里,一批设施现代化的室内冰场开始崛起,国贸、西单、崇文门新世界迅速云集了一批更年轻的滑冰爱好者,退役运动员也开始提供专业教学,“大部分以花滑和短道速滑为主。”北京业余滑冰经历的沉寂,让现在圈子里缺乏三四十岁的冰友,80后小石是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因观看2006年冬奥会的一场速滑比赛“动心”,他在地坛公园外的紫龙祥滑冰馆报了速滑培训班,“这项运动一往无前,无论是身体姿态还是蹬冰动作,都是围绕着如何突破速度极限展开的”。
小石的第一双冰刀是在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店花1700元购得,刚参加工作的他工资大约2000元,往前30年,宫延利在利生门口找二道贩子花18元也买了第一双冰刀,当时工资32块5,“但原来是老式死托冰刀,我学冰已经改为拖拉板式冰刀了。”小石记得,1998年,“克莱普”拖拉板式冰刀在长野冬奥会上首次亮相,为速度滑冰带来了新突破。
对于变化,宫延利是敏锐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冰场里开始出现“老友重逢”,“很多扔了滑冰十几年的又捡起来了。”借着回潮,他所在的俱乐部自2009年连续举办了三届民间轮滑比赛,人数从几十人涨到四五百人,参赛者一度覆盖了11个省(区、市)。民间的热情很快触发了官方的推动,尤其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后,一批场馆和大众赛事为滑冰爱好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去年盛会的成功举办,更将民众的冰雪热情进一步释放。
“现在的孩子直接上冰丝带,条件太好了。”何广深坦言,得益于器材、场地和教练专业性的提升,现在滑冰的青少年水平不容小觑,但他强调,滑冰是颇具技术含量的运动,坚持并非易事,他记得,年轻时遇到专业队,总琢磨为何追不上人家,虚心请教后才只知道体能和技术缺一不可,因此,他每天上午4点起床开始跑步、打羽毛球,“一年三季都在练体能,就为了冬天露个脸。”如今他依然坚持轮滑和体能训练,保持健康活力的同时,也会为路人一句“嘿,这老爷子滑得真漂亮”而喜悦。在他看来,倘若现在的青少年也能坚持,滑冰的热潮还将重现。
但在崔克岭看来,如记忆中那般真正的“滑冰热”,除了群众参与,主管单位、场馆及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从业者也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虽然原来条件没现在好,但冰友在冰场上讲规矩,场馆在服务上也更细心。”他表示,往日值得回味,必然有让人温暖的地方,“希望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能把过去一些好的经验再捡回来”。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北京滑冰往事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禹唐体育原创文章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