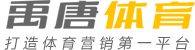露营、野餐、骑行:只要不待在家里,去哪都行
作为旅行的替代,那些传统户外运动正在城市周边的山野中兴起,从爱好者群体拓展到普通市民。
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之间,纵贯着一条河流,名叫温榆河。河岸这两年铺上了草坪、绿道,环境整饬一新。今年开春以来,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温榆河两岸都像长蘑菇一样撑起一顶顶帐篷,延绵数公里。市民们扶老携幼带着狗,在河边度假。河畔开满紫色的二月兰,即将进港的飞机低空飞过,在河面投下倒影。清明假期,定居北京的歌手王啸坤在抖音热情地推荐过这里,“千万不要再去那些人挤人的地方,路边一停车下来就是,”他伸开双手拥抱空气,“真舒服,真舒服⋯⋯”
东三环的亮马河已经成了北京的塞纳河,聚集着半个城市的年轻人;而东五环外的温榆河畔,则是北京的上野公园,是家庭聚会的地方。
到了5月,北京有一阵取消堂食,来河边野餐的人更多了。很多人连帐篷也不带,只用一张天幕撑起一个下午的阴凉。更简洁的人,就在河埂路旁支起简易的炉子烤肉,或者坐在野餐垫上吃吃熟食。当精致露营、风格露营或野奢露营在各城市甚嚣尘上之时,温榆河边的露营和野餐,却既不精致也无风格更不奢侈,只跟“野”字沾点儿边。此地的主流帐篷是三四百块一顶的迪卡侬馒头状的快开遮阳棚,烧烤炉锈迹斑驳,没有人举着相机拍美照,也没人对着手机直播。人们朴素地相聚在河边,实在只是因为没处可去了。
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旅行和聚餐都因疫情被暂时取消。到郊区去,到户外去,成为城里人的肉体和精神归宿。
作为旅行的替代,那些传统户外运动正在城市周边的山野中兴起,从爱好者群体拓展到普通市民。徒步、登山、骑行、攀岩、垂钓、探险⋯⋯以及露营和野餐,有多少并未接触过户外的“小白”,在这一年春夏时节采购装备,一身运动装束,进入城市附近的荒野。
“此时不骑,更待何时”
5月下旬,黄国松骑着自行车走了一趟昌平慈悲峪线,绕十三陵水库而行。此行主要目的是练习爬坡,100公里的路线骑下来,痛苦得“绝望”。这是他的爬坡初体验,一个月前他才开始骑行。他并不热爱骑车。
对他而言,骑行只是健身的替代品。5月,健身房因为防疫关门了,为了填补空下来的时间,并保持运动量,他入了骑行的坑。他的车是一位朋友前几年留给他的二手车,3000多块钱的入门款美利达公路车,通体漆黑。
黄国松更喜欢城市夜骑,晚上9点多出门,在城内骑两个小时,行程四五十公里。有时从北边的鸟巢骑到南四环,再沿中轴线直插回来;有时骑到西边的新首钢大桥,眺望冰雪大跳台;有时在东城的胡同里转圈。他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北京夜色,王府井、三里屯等繁华商圈灯光暗淡,但商场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像开运动会一样,打网球、打羽毛球、跳绳、玩轮滑和陆冲板的都在挥汗如雨。三里屯太古里的广场上,人们都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不像以前穿得光鲜亮丽,一群大叔举着相机街拍,现在风景完全不同。”
骑行是4月以后在北京走红的。当月上海因疫情全域静态管理,寸步难行的压抑通过互联网扩散开来;5月,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区遭遇封控。商场关门、演出取消、公园关闭、游乐场封闭、堂食暂停、学校停课⋯⋯户外活动成为最后的去处。黄国松清明节开车去郊区转山时,山里人还不多,5月再去,骑行道上都快堵车了。来回100公里以内的妙峰山、戒台寺、潭王路、黑山寨等线路上,满脸兴奋的“小白”比比皆是。
这个春天,骑行圈里弥漫着一种“此时不骑,更待何时”的情绪,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封控,所以趁着还能出门,赶紧骑车上路。北京骑行爱好者林好男今年4月的骑行里程接近1700公里,爬升1万多米,双双达到7年骑行史的新高。4月之后,骑行组织停止召集集体活动,坚持上路的骑友要么独行,要么以两三人小规模团队出行。林好男说,两位骑友碰头,会互相出示核酸证明,自证阴性。“现在不骑的话,可能过两天突然就不能骑了,一种强烈的未知感和无力感催着你出门。”他说。
阅读和骑行是林好男的两大爱好,在这个特殊时期,两者都延伸出特殊的意味。他将阅读看作是内心的流亡,而骑行则是外向的抵抗,后者更易被环境威胁。因此对他而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骑行的优先级要先于阅读。
4月,在骑行房山“六石-红井”线那晚,他跟同伴在漆黑如墨的山路上,借着前灯反爬松树岭回城。停在路边休息时,同伴突然让他抬头看看。“看见北斗七星了吗?”同伴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位同伴是在路上偶遇的,强烈拉拢他一起去红井路。在林的计划中,“六石-红井”本该是两天的行程,他加入了这个疯狂的任务。“当天的旅途中,他不断聊起经过的村庄有何历史变迁,太行山与燕山的形貌又有多大不同⋯⋯”林好男回忆说,“重要的不仅是骑行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还有它带来的强烈暗示:保持乐观,保持好奇,不要让生活的疲乏与荒谬战胜自己,至少要抵抗得更久一些。”
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为被归为“非必要”,作为旅行、聚会、聚餐、遛娃替代品的城郊户外活动,就成为某种程度的必要。
“我觉得户外会越来越热,太多玩法还没开发呢,徒步、登山、露营、骑行、越野跑、冲浪、潜水、帆船、桨板、皮划艇、攀岩、攀山、滑雪、钓鱼、高尔夫、骑马⋯⋯”说这段“贯口”的时候,李轩刚刚将新到货的钓鱼竿拆箱,在店里上架。他创办的James outdoorlife户外品牌店位于北京顺义天竺保税区,临近首都国际机场,主营露营装备,现在扩展到徒步、钓鱼等品类。6月1日下午,一个小时之内,就有四拨朋友来到店里看装备。
林虹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那天下午3点多,她带父母和儿子来到李轩的店里,他们家今年开始置办露营装备,已经买了“一室一厅”的帐篷、两个床垫、折叠桌椅、炉具等,花费近万元,这次想找几把更舒适的椅子。这些东西差不多已经塞满她家的SUV了,但她还想买一台车载冰箱。
疫情后,她常跟朋友在郊区聚会,称之为“荒野聚会”,有时也在朋友郊区的小院里开篝火晚会。初次买装备时,她随便预订了一些,后来在朋友的专业指路下,换成了全套国际知名户外品牌,一个800块钱的桌子换成了1800块钱的。她觉得疫情过后,露营也不会停止,装备会一直用下去。“我们没在郊区买房,这些装备相当于在郊区有了一室一厅,这么一想,还挺划算的。”她笑着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夫妻在大学当老师,有定期海外旅行的习惯。日渐殷实的经济状况,带来上升的生活品质追求,当疫情搅乱了这一切,撕碎了旅行计划,城郊户外活动就几乎成为中产生活的一项标配。
“表面上是露营、烧烤,背后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周末团聚的精神需求。同样的,户外运动也反映了大家探索世界的需求。”李轩总结道,“这些需求不是悬浮的,是立得住的。”
户外的理由:自由、孤独与交互
5月17日,张清扬登顶了人生中第一座雪山——云南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她37岁,定居深圳,在互联网公司担任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职位,也是一个9岁男孩的妈妈。那天天气极差,向导说是罕见恶劣天气,但她决意一试。此前两次雪山之行她都止步5000米海拔之下,这次一定要突破极限。
最后几百米,队友们陆续下撤,决定性因素是手套。他们的手套都湿透结冰,继续前行会冻伤双手。而张清扬在标配的一厚一薄两副手套之外,额外带了一副厚手套,最终护卫她登顶。同行五人中,只有她抵达了刻着“5396米”的木牌。
为数不多的几次登山,都遗憾地遭遇了坏天气,她从未见过传说中雪山之巅“一眼万年”的美景。可即使是风雪满天、雾锁重山,在她眼里,已然是不虚此行的奇观。
张清扬有三年户外经历。2019年5月,她跟随领队第一次涉足雪山,爬到4800米海拔时,狂风骤起,另一支队伍中有人滑坠,领队决定原路下撤。这次未完成的哈巴雪山登顶,是她户外生涯的起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她的户外生涯在疫情两年里见缝插针地起步,每个五一、十一和暑期,她都在户外,登过四姑娘山二峰,完成了环青海湖骑行、洛克线徒步、梅里北坡徒步。“每次从户外回来,我都觉得自己又版本迭代了。”户外是她为自己找到的获取内在能量的新方式,“尤其像这次疫情,突然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焦虑的情况下,你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登山能给我这种动力。”
登山是最为经典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18世纪的欧洲,因探险和科考而生的登山、穿越和徒步,开启了现代户外运动。中国于1956年成立国家级登山队,背负国家任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而民间的登山队迟至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中国民间户外运动至今不过30余年历史。
在深圳,登山正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深圳周边并没有千米海拔的高山,但疫情之后,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将周边十座山峰打包成“深圳十峰”概念,鼓动起群众性登山热潮。在小程序里打卡十峰的人数已超33万人次。深圳十峰上还出现了一支醒目的童子军,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爬山,也有公司组织专门的儿童登山活动。山,成了“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新去处。张清扬9岁的儿子已经达成十峰全部登顶的成就,曾经分头补课的小伙伴,现在时常在山里相聚。
被疫情激发的户外运动潮,并非单纯出于对大自然突然而来的热情,首先是来自对行动自由的珍视,以及被压抑的社交需求。疫情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城市生活的脆弱和狭隘,而广阔的原野,蕴含着自由与生机。
2020年之前,张清扬常常去海外旅游,她觉得旅行是“由外而内”的过程,将看到的风景内化为记忆;而户外运动则是“由内而外”,在与身体的较量和内心的对话中获得感知,两者对她都不可或缺。而在海外游停滞的几年,远离城市的户外运动,实际上也成了旅游的平替。她说,一些东西丧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可贵,所以现在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她都很珍惜。
对骑行新手黄国松来说,骑行不仅是健身的替代,同样是旅行的替代。他是重度旅游爱好者,周末很少待在北京。疫情之后,他花4999元买了航空公司专门开发的“随心飞”套餐,随时抢票出门,半年里跨省旅行三四十次,飞遍大半个中国。最近半年他足不出京,但心里“每时每刻都想出去”,骑行只是无事可做时,不得已的选择。
疫情让生活陷入一种不确定的临时状态,出门这件小事变得重要甚至奢侈。此时此刻,户外运动给予人的自由感,在反衬中被急剧放大。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里很小的空间,当你骑到六环之外,会看到一个不像北京的北京。眼前的道路是无限延展的,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刻。”林好男说,当他晚上再骑回高楼大厦和红绿灯的世界,反差感非常强烈,就像刚刚完成了一次旅行。他最初喜欢上骑行,是因为能快速地逃离日常生活。他是一名互联网公司资讯编辑,每天坐班8小时,经常上夜班。只要跨上公路车,出走50公里,就能抵达一个开阔而陌生的地域。与其他运动相比,骑行只需要一辆车和一个好天气,极具自由精神。接触骑行之前,林好男的爱好是登山。他觉得骑行和登山各有动人之处,骑行比登山走得更快、更远,与自驾相比,骑行又是以肉身进入自然,用全部感官接受自然的信息。
“身处峡谷,哪怕只是片刻,你便能感受到人类有限的感知和善变的臆断。百年、生命、年代、春秋、昼夜、心跳,这些你熟知的时间标记在此处消隐无踪。”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曾在英伦群岛上寻找荒野,在《荒野之境》中,他如此描述置身荒野的感受。他接着写道:“峡谷外那个充斥着商店、学院和车流的繁忙世界,似乎不复存在,就连我的家人、故乡,还有硕果满枝的苹果园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无论在雪山还是荒野,户外运动多数时候都是一件孤独的事。张清扬说,就像苦行之旅,只能跟自己对话,在克服困难中感受内心的变化。为什么会喜欢上孤独的运动呢?她觉得,户外运动让她真切地感觉自己强大了起来。“这种强大是真实可见的,不是鸡汤,当你凭借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意志力,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标,那种力量是很真切的。”作为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中层,这几年的工作并不省心,她需要内在能量的支撑。
另外一些人则与她完全相反,走入户外的动力之一就是社交。
十多年来,年轻人的社交性娱乐活动迭代了数次。一开始是雷打不动的“吃饭+唱K”;后来,桌游、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室内活动取代了KTV;现在,户外运动因疫情和社交网络走红。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领队徐思朋感受明显:近两年加入的徒步者,“从小红书过来的不少”。社交网络让一些户外运动火成了社交货币,在线社交日益熟稔的年轻人,其实正在逐步丢失线下交友的渠道,户外运动成为一种新潮的补偿。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则不无得意地说,糖粉俱乐部里已经结成了八对夫妻。
危险不可忽视
今年5月28日,一段妙峰山深夜飙车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夜色中,两辆改装汽车在狭窄山道上追逐,引擎声震天。视频传开5个小时后,北京门头沟警方控制了两名嫌疑人。这段妙峰山山道在北京颇有名气,是摩托车和自行车骑行圈里的经典线路,也是天然的段位标尺。
妙峰山上有一段21公里的上坡段,60分钟之内爬完坡,为大神级别;60到90分钟左右,是高手级别;90分钟以上,算一般水平。2014年第四届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中,国际自行车联盟将妙峰山坡段的难度定为“hc”,这是世界最高难度等级,官方盖章让妙峰山在北京骑行圈拥有了秋名山一般的地位。骑友们根据妙峰山坡段的成绩为自己测定段位,骑友群发布招募启事时,会注明是“休闲局”还是“大神局”——“休闲局”往往以社交休闲为目的,而“大神局”意味着这是以竞速为目标的高手过招,将会苦不堪言。
这些户外局大多由各项运动的俱乐部发起。北京户外运动以民间自发组织为主,日常性地在京郊举办;而官方部门则会组织规模更大的活动,往往具有节庆性质。
疫情之后,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的微信群扩充了五六个,增员两三千名,增速翻番。“没法儿去外地了,好多人就来徒步了。”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领队徐思朋说,北京各类徒步俱乐部、组织至少有100多个,北京徒步者CLUB群友就有近1万人,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说,北京成规模的骑行俱乐部至少有几十个,成员三五百人,车店发起的俱乐部则有多达千人,而更小的团体和专项车队更是每天都在生长,难以计数。
户外运动暗藏危险,组织者时刻紧绷着弦。雪灵介绍说,骑行活动的准备非常繁琐,要掌握路线情况和交通信息,要预判天气的变化,还要了解每个参与者的体能、经验和最近的身体状态,“安全永远是第一。”北京徒步者CLUB则每次都会为参与者购买高额意外险。
周末到来前,北京徒步者CLUB在小程序里发布数条徒步线路的人员征集,每条线50人封顶,由领队带领,走向郊区。他们设计了一个强度公式,代入里程、爬升、路况、负重等数据,就能算出线路的运动强度,从而确定出休闲、初级、中级、大强度几个等级,以分类招募徒步者。最近,他们规划出一条名为“太行之巅”的大强度路线,串联京郊2000米海拔以上高点,贯通140千米,计划用时一天一夜,只有体能与经验俱佳的高手方能参加。
大量新手突然涌入户外运动圈,令资深户外爱好者们喜忧参半,忧的是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者热衷于拍照打卡,那些带着滤镜的照片和视频,将“小白”们吸引到荒野之境,也带至危险边缘。去年,在深圳七娘山,一位登山者为了登高拍照,失足掉落100多米深的悬崖,救援队找了两天才找到遗体。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高级户外教练谢孝军当时就是救援队的一员,他对以拍照为目的的登山行为深恶痛绝。“照片展示给你的是最美的一面,但它不会告诉你,为了拍出照片你要经历什么危险,有多少人摔下去过。”仅他所在的救援队,一年就要出动三四十次。
谢孝军说,绝大多数登山事故都出自人的无知。“登山不是两脚走路而已,是个系统工程,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他强调再三。去年6月,他带队攀登广州从化一座几百米的黄茶园山,途中起风下雨、气温骤降,还好他出发前提醒队友带了羽绒服,避免了失温。“6月份在广东要穿羽绒服,没人能想到吧?”他每次登山都会带一件薄羽绒服,以及雨伞、头灯、手电筒,这些小玩意儿可以救命。
谢孝军提醒,登山至少要四人成队、两人同行,切不可单独一人。“比方说一种很简单的情况:你脚崴了,又没有信号,怎么办?如果有人同行,就没问题。”他建议登山者都要参加专业培训,很多登山多年的人都缺乏必备知识,没遇到危险情况只是运气好,“但你运气不可能总这么好吧?”
骑行的危险在于速度,速度的快感与危险,只有一线之隔。无论在空旷的山路还是拥挤的城内,危险都相伴而行。在山里放坡路段,老骑手会冲到80公里时速,北京环路的汽车最高限速也就是80公里,谨慎的新手也会达到三四十公里时速。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亲眼见过两个骑手在山路上高速相撞,幸亏戴着头盔,只造成轻微脑震荡。资深如他,也只敢骑出三四十公里时速,但他见过胆大的新手飙得飞快,看得心惊肉跳。
而在城里,骑行的危险因素更多、更复杂。2017年,雪灵骑行时,前方一位共享单车骑手在路中央突然下车,然后推车向左逆转,左后方的雪灵血压飙升,瞬间捏死车刹。一秒钟后,他已经躺在地下,左臂骨头断成三截。半年康复期内,他采用运动员的运动康复法,每天忍痛撑直胳膊,把刚长起来的组织撕开,避免“长死”。就像用刀子割自己,每天一次,他的胳膊才得以在康复后完全展开。“鬼知道那时候经历了什么,”他痛苦地回忆,“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人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康复之后,他就组建了骑行俱乐部,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教新手安全知识。人们往往将变速车骑行与共享单车或普通单车骑行等同,其实并不相同,变速车危险性远远高于普通单车,“如果你没有形成肌肉记忆,速度起来后来不及操作,要么撞车,要么翻车。”而城市道路规划也并非都考虑到骑行需求,专为休闲建设的绿道,往往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前几年跟主管部门交流,发现当时的共识是,绿道只服务于走路和休闲。近两年情况正在改变,比如北京朝阳区正在建设138公里贯穿公园的绿道,可以骑行通过,“最近国家部委发布的8万公里绿道政策里,就有骑行通过的说法了,当然还需要更多的部委来支持。”杨新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每一项户外运动都有风险,即便是看似休闲的露营,也潜伏着失火、一氧化碳中毒、湿气、涨水等危险。玩家一窝蜂涌入,但有效管理尚未覆盖之时,正是亟须警惕的危险高发期。
充分准备、量力而行、逐步进阶,新手应该循着这一路径投身户外运动。虽然对装备有深深的迷恋,但李轩并不提倡做“装备党”,他对户外新手的建议是:先走出去,从野餐开始。就像温榆河畔的“迪卡侬式”露营者,在长安街上,也不乏相约扫一辆共享单车夜骑的人,同样快乐。
李轩觉得,当下的户外文化仍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实你弄个蛇皮袋野餐也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自由一些,返璞归真一些,不要轻易被那些照片给‘勾引’。”
如今,户外文化被舶来自西方的几项运动所框定,要知道,那些主流户外运动和休闲方式的诞生,均与彼时彼地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乃至精神面貌直接相关。欧洲的户外运动是冒险精神的外化,美国的露营由房车普及直接拉动,日本人对帐篷的亲近,则与应对多发灾害而锻炼的生存技能一脉相承。
户外本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在中国传统中,亦能追溯到对山水田园的天然亲近。文旅专家、美学内阁创始人莫克力有一个缥缈的期待,或许中国也能发展出更亲近我们自身的户外方式,比如采摘和劳作,她笑着说,“因为我们来自农耕社会,劳作会让我们产生亲切感和安全感。”
(应受访者要求,林虹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露营、野餐、骑行:只要不待在家里,去哪都行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禹唐体育原创文章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