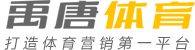英格兰人眼中的英足总是怎样的存在?
“足球比政治更关乎政治。”——2004年,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oran Eriksson)
“足球比政治更关乎政治。”——2004年,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oran Eriksson)
也许我们总要透过外国人的双眼,才能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那就是,足球是一场政治游戏,但凡牵扯到权力、金钱和地位,总免不了会有一番争斗,以决定谁来制定规则、谁能分到好处、荣耀归谁所有,何况足球界是三者兼备。英格兰足球过去自认刻意排斥政治,但最近20年来,却变得高度政治化,这个过程并不令人兴奋。历来多位体育大臣都被英格兰足球的管理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休伊-罗布森是其中之一,他曾在2011年表示:“英格兰足球是国内管理最不牢靠的运动。”
认定自己最权威
当然,足球也不是没有对手,赛马和拳击以及这两种运动与赌博产业盘根错节的关系,就让政府伤透了脑筋。其他热门运动项目,如橄榄球、板球和网球管理单位也都因为组织僵化和欠缺专业而备受嘲弄。英格兰足总与国内大多数运动管理单位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足总的未来展望、制度结构和核心要员相比之下,更加无法胜任眼前的挑战,况且受到了媒体报道(不说是监督的话),也高出好几百倍。
英格兰足总当初成立的目的并不在此,因为面对外界点名,英格兰足总极度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权威及其在足球界众多利害关系之间交涉协商的政治角色。英格兰足总首先自认定为“足球的监护人”、规则的发明者和持有者,致力于提升及发展足球运动,这当中不包含商业利益或意识形态。于是,英格兰足总向来认定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主掌机关,是足球界的合法最高权威。足总自己的简章手册内页就写着“英格兰足总授权发行”。这是一种宣示主权的做法,就像国会议事规范和行政命令上也有的一样。
然而,英格兰足总其实没有那么庞大。它一直自诩是一个志愿团体兼业余组织,没有制式的管理构架,也未受到商业主义的恶邪影响,能够营运靠的多半是自愿劳动、安排业余竞赛和指导训练。足总的主权和管理概念首要着重于,让足球不受国家机关和市场机构的入侵。市场方面,英格兰足总在1880年代才与职业足球和足球联赛达成不稳定的平衡。如我们所见,足总的确靠着限制俱乐部董事的薪资和分红,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对职业赛事经济的掌控,但转会薪资与其他事物的细节,仍有很大一部分留给英格兰足联决定。这样的权力平衡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战时状态下,政府的介入曾短暂受到容忍。一次大战爆发时,战争部门兵员需求量急剧上升,足总曾充当招募士官,之后又成了民族主义的代罪羔羊,因为在战争进行的同时还继续踢职业比赛,因而被贴上不爱国的标志,直到赛事终于在1916年终止。二次大战期间,英格兰足总协助安排友谊赛计划,如今公认对士气有所帮助。战争结束以后,国家收回令箭。
时任英格兰足总秘书的斯坦利-劳斯(Stanley Rous)认为这是美事一桩。他在1952年写下这段话:“原子弹和燃烧弹留下的恐惧还未飘散,在这样的世界里,足球场是少数依然保有理智与希望的地方。”另一方面,博尔顿在1946年发生博登公园球场(Burnden Park)惨剧,33人因看台上的推挤践踏丧命,受害者或许会希望国家出手加强介入,逼迫英格兰足总和各家俱乐部采取《休斯报告》(Hughes Report)提出的改革意见。
能力不够,麻烦不断
到了1980年代中期,英格兰足总的政治与经济自主权开始瓦解。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比赛发生骚乱的频率和警方出动的规模使得政府大举介入成为必要。海瑟尔和布拉德福德城两起惨案,让足球成为讨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希尔斯堡惨案及判决后的风波,让整个足球产业与国家形成一种长久、乃至于半永久的关系,就和现在一样。与此同时,豪门俱乐部早期的商业化发展,组成超级联赛的耳语,以及付费电视转播金的承诺,开始加快英格兰足球转变的步调。英格兰足总光是要跟上这些商业与政治变化,就已经够难了,但足球管理的课题,还会变得复杂百倍。
英格兰足总现在必须和国际性组织交涉,如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和欧洲执行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同时也开始面临基层倡议者的挑战,包括球迷团体、球迷共有运动(Fan-ownership Movement),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人士,点出存在于足球界的不平等和排外结构,相同的还有性别、身障、种族与性取向的问题。英格兰足总秘书弗雷德里克-沃尔(Frederick Wall)从来无需处理性别预算(Gender Budgeting)的概念,斯坦利-劳斯也不必回应公平机会促进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但是现在他们的后继者却必须这么做了。经纪人、投注商和赞助商都曾只是微不足道的抉择,如今却跃升至新的地位,带给英格兰足总一连串新的难题。
除此之外,英格兰足总还必须面对一个一夕之间变得比以往更强大、更飘忽不定,也更加全球化的足球产业。英格兰足总本身的资产负债表,最能呈现此变化的规模。1980年代晚期,英格兰足总的营收约有300万到400万英镑,盈余几乎全数来自温布利球场销售的门票。
为英格兰国家队签下球衣赞助合约,只有数十万英镑之多,不像现在有上百万英镑。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觉得这样做很庸俗。到了2011年,英格兰足总的营收超过3亿英镑,赞助商以及足总杯和英格兰国家队的赛事转播合约各自就赚了近1亿英镑,温布利球场的商业债务(Commercial Debt)又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话虽如此,即便有这种程度的成长,英格兰足总的经济规模也只不过和单一家大俱乐部一样,比起英超联赛整体,更是小到不行。
与规模问题一样,难解的是复杂性的问题。从前,英格兰足总只需对应一小群相对知名的报章媒体记者,关系好的时候亲密无间,坏的时候顶多也只是相敬如宾。但媒体生态和新闻需求在1980年代出现变化,除了老班底足球媒体以外,现在还多了经营八卦小报的肮脏商人、众多新成立的运动及新闻频道、24小时不眠不休派出的新闻狗仔、持续扩张的海外媒体集团,以及商业财经版面偶发的采访。
英格兰足总常年以来早已习惯了与内政部和警方交涉,但在新的环境下,足总发现自己几乎必须和政府每一个部门沟通。外交部曾对国际足球嗤之以鼻,现在却还审慎商议国际锦标赛的标案。
足总发现自己要与税务海关总署商谈足球界内各种不堪入目的会计手法,与新成立的文化媒体及体育部讨论温布利和奥运等全国性赛事,还要与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沟通。这些单位有意用足球当作推动社会计划的基础,国会对英格兰足总的兴趣也日渐增加。从2000年起,文化媒体及体育部的委员会几乎每年都会就足球管理议题发表报告,跨党派议会的足球团体也同样多产。这反映出,国会有一群位高权重的政治阶层,头一次能够认识足球,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足球建立关系。
国际政治对英格兰足总而言也并不容易驾驭。1948年重回国际足联以后,英格兰足总在这个世界级理事机构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特权和地位。斯坦利-劳斯的主席任期从1963年持续到了1974年。之后,国际足联选出新任主席阿维兰热,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英格兰足总仅有的些许善意和政治资本随之消失殆尽,对于足球外交新规则也很悲哀的缺乏学习能力。
欧洲层面的政治情势一样令人担忧,欧冠联赛的成功赋予欧足联莫大的权力,英格兰足总极力想在欧足联的权力脉络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欧盟、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法院,最近20年来都针对足球做过裁决,包括介入规范劳动合约、电视转播、市场运作和国际足球管理的廉洁问题等。
组织陈旧,一潭死水
即使是最柔软、最灵活的组织,要应付上述情况,也是难事一桩,况且英格兰足总并不柔软,也不灵活。相反的,英格兰足总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犹如谨慎拘泥的地方政府与保守排外的守旧组织相添作伙,用“兰卡斯特门”(Lancaster Gate)一词代称,正是恰到好处。
1910年到1929年间,英格兰足总向大英博物馆承租了罗素广场42号(42 Russell Square),那地方貌似鬼屋,办公室即使是供英格兰足总使用,也嫌太过泛黄陈旧。在这样的情况下,搬进西伦敦的兰卡斯特门12号看似是跨越了现代世界,可其实也没那么现代。这里从前曾是寒酸的伊甸花园饭店(Eden Court Hotel)和英国洗衣工与清洁工协会的总部。
斯坦利-劳斯出任足总秘书时,明显对这个地方兴趣缺缺。他写道:“英格兰足总在很多方面像是一潭死水。我1934年8月4日来到这里任职,停我的中型轿车也不成问题,因为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员工一共才五个人。”在劳斯和他的继任者执掌下,兰卡斯特门是一个迷宫般的走廊和沉闷会议室组成的世界:打印机和皮面精装的卷宗;开会、道歉,修正会议内容与其他事项;有足总杯抽签用的木球和皮袋,还有阿尔弗-拉姆赛的鬼魂在喝早茶。刚从BBC派来的大卫-戴维斯也吓了一跳:
“走进1944年的兰卡斯特门,仿佛回到了1894年。我仿佛置身在比较近代的博物馆,一幅褪色的女王肖像画向下俯视,画中她还是那样年轻。壁橱布满灰尘,玻璃门后摆着银质奖杯,来自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地方,有些老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英格兰足球的管理机构上班朝九晚五,从周一到周五,中午有一小时午休。足球却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在进行,通常周末特别忙碌。”
但那个时候,1990年代初期的英格兰足总,执行官把拆别人的信当成例行公事。技术与宗教部门的总长对职业比赛极其陌生。组织的媒体运营更只能以可笑来形容。在任用戴维斯以前,英格兰足总依赖的新闻官的作用约等于菜鸟,甚至未曾想过应该建立一个通讯部门,思考与媒体互动的策略。尽管与政府措施和立法的关系日渐错综复杂,英格兰足总却没有专职机构以联络官员或任何智囊团。英格兰足总极其缺乏商业与政治层面的经营手腕,以至于连肯-贝茨都能被视为是主管新温布利球场建设的合适人选。
领导年年换,政策朝令夕改
不过就某方面而言,英格兰足总雇佣怎么样的人、成立什么部门,其实都不重要。问题出在足总内部的地位与权力阶层。员工地位始终低下,生杀大权和关键决策都掌握在足总委员会和足总理事会手里。会内成员又任职于多个级别的委员会。英格兰足总运作的骨干就是由这些委员会形成的。面对21世纪崭新且更复杂的政治环境,最终却是这样的体系要带领英格兰足球向前进。
只需要稍稍瞥一眼英格兰足总委员会的组成,就知道与19世纪多么相近。委员会成员包括职业联赛的代表,但人数只在少数,大部分成员是足总本身地方区划架构的代表,多半是中产阶级的志愿者,外加零星几个享有制度特权的足球协会,如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私立学校和业余俱乐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有一个,其次给剩下所有大学体系。
大英国协的俱乐部依然隶属于英格兰足总,直到1980年代在委员会都拥有席次,代表人数轻易就超过了英格兰女足总会(Women’s FA)。然而,委员会的效能始终有限,一年仅召开六次会议,会议开到中午就结束,很少出现什么有意义的简报,倒是喜欢挪用其他地方批准的提案。
所谓其他地方指的是英格兰理事会。它负责管理对外关系、日常行政权力,及制定改革章程。权力在此看似由业余足球和职业足球共享,但过去20年来,职业足球对所有重大议题都能够实行否决权。理事会没有独立于外的角色可以进行反驳。业余足球以及国家足球的代表,从来未展现出挑战职业足球的政治决心,反而成了拥戴者,向英超和英格兰俱乐部联赛收取可观的金钱补助。在如此动荡复杂的年代,一个在平和的世道下创建的组织,不免会感受到压力和失能。在英格兰足总,资深员工与官员淘汰率越来越高,尤其让这个问题浮上台面。
早年,拉姆塞、格林伍德和罗布森三人就包办了英格兰足总教练的职位近30年。布莱恩-罗伯森卸任以后,从泰勒到霍奇森,短短20多年英格兰队就吃掉了七名教练。
英格兰足总理事会主席以往的任期也比较长,从1966年到1996年只有三人,出任主席的分别是安德鲁-史蒂芬(Andrew Stephen),来自谢菲尔德的苏格兰博士;哈罗德-汤普森(Harold Thompson),作风专横的牛津大学化学家;还有伯特-米利奇普(Bert Millichip),一个亲切但无趣的律师,来自西布朗维奇。米利奇普退休之后短短几年,英格兰足总就换了五任主席。基斯-怀斯曼(Keith Wiseman)因卷入受贿罪丑闻而辞职,饱受揶揄的杰奥夫-汤普森(Geoff Thompson)大半时间身形薄弱,此后很快又有崔斯曼爵士(Lord Triesman)、大卫-伯恩斯坦和格雷格-戴克连番接任。
秘书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更低,也呈现相同模式。弗雷德里克-沃尔和斯坦利-劳斯几乎包办了20世纪的前60年。丹尼斯-法洛斯(Denis Follows)、泰德-克罗格(Ted Croker)和格拉汉姆-凯利(Graham Kelly)各自在任约10年,直到凯利被迫与怀斯曼一起离职之后,风声风水轮流转的特别快。克罗泽只任职两年,就因为改革热情与英超的政经利益相互矛盾而被撵走。
接着,马克-帕里奥斯(Mark Palios)在特雷米尔流浪者队和克鲁亚历山大(Crewe Alexandra FC)队当过职业球员,曾是会计业巨头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简称PwC)的合伙人,更别说曾获选为2003年度“重振资本家”(The Around Financier of the Year 2003)。但这个完美人选只做了18个月,因为帕里奥斯与英格兰足总总部秘书法里亚-艾朗的婚外情曝光。他的公关团队企图掩饰,但手法笨拙,反而让这件事加倍棘手。
布莱恩-巴威克(Brian Barwick),经验丰富的运动频道CEO,成功撑了四年,但因为新任主席崔斯曼爵士怀疑他的政治能力而被解雇。接班人伊恩-沃特摩尔(Ian Watmore),虽然有能力应付白厅扑朔迷离的电子政务计划,还负责首相服务传递小组(Prime Minister’s Delivery Unite)的运营,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受不了缓慢的改革步调和组织内部改革的强烈反弹,愤而辞职。略去大卫-戴维斯的短暂接管不算的话,亚历克斯-霍恩(Alex Horne)在2010年走马上任,成了短短十年内第五任英足总CEO。
就某个角度来看,很容易会以为英格兰足总做得并没有那么差。虽然受累于本身过时的自我定位以及勉强屈就的决策结构,英格兰足总毕竟还是不断的追赶着世界足球的变化。不过,这也只是一时的念头罢了,看看足球管理上的政治斗争,就知道英格兰足总其实是在自己创业自己担。
本文转载自懂球帝,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别黑中国足协了,来看看英格兰人眼中的英足总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禹唐体育原创文章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