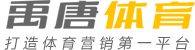解放空间还是卖命揾食?城市极限运动的前世今生
11月8日起,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吴咏宁的微博永久停更。近日,他的亲友确认他在长沙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亡,令人无限唏嘘。
11月8日起,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吴咏宁的微博永久停更。近日,他的亲友确认他在长沙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亡,令人无限唏嘘。“我一定是玩得最狠的那个,因为我每天都在爬,我是在玩儿命。” 吴咏宁曾这么说。
并不是每个高空挑战者都像吴咏宁这样“玩儿命”,但是惊险刺激的城市极限运动确实越来越红,逐渐走向大众视野。高空挑战是城市极限运动的一种,英文为“Rooftopping”。2010年,加拿大多伦多一位名叫Tom Ryaboi的青年男子和朋友在高楼的屋顶拍了一组照片:双腿悬空坐在如同悬崖的高楼顶上,楼下汹涌的人潮如蚁群。这些视角奇特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热潮。自此,高空挑战流行开来,展示的方式也从照片发展到视频,难度逐渐加大,挑战者开始试着在高楼顶层做一些动作,更加震撼、更有冲击力。
迪拜,一群极限运动爱好者登上一座高楼楼顶。
这样的极限运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因其安全性、合法性和对公共空间的侵入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在吴咏宁去世之后,网上有些评论认为拿生命危险养家不值得提倡,引发了一些争议。
城市极限运动既有彰显自我价值、展示自由的运动精神,挑战、反抗权威的作用,也同时卷入了商业化带来的消费刺激。当这些特性共同出现在没有标准和规范,又涉及生命安全的灰色领域时,城市极限运动该何去何从,实在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追寻自由 城市化与极限运动的兴起
极限运动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流行趋势。近几年,YouTube等网络自媒体平台里播放量最高的视频中,极限运动占很大一部分。除了常见的滑翔、高空跳伞、滑雪、攀岩、冲浪等野外项目,高空攀爬、跑酷、街道滑板这些和城市相关的内容也非常多,且逐年增长。日常生活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变成了极限运动的一部分。仔细探讨极限运动的兴起源头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其走向城市的发展途径几乎是一个必然。
极限运动起源于60年代的美国,其诞生和人类天性息息相关的冒险刺激不无关系,但其社会背景也不容忽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发展史上的最辉煌的时代,也正在步入后工业时代和后现代社会,虚无、消解中心、反理性、个性主义和多元化价值观等思潮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解构了宏大的现代叙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同于传统的强调比拼结果的竞技体育,主张个人体验和个性自由的极限运动开始出现。传统的体育项目更多以距离、高度、时间等客观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运动结果,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但极限运动却并不要求严格客观的衡量,而更多以参与者的心理需求或自身体验为主要标准。这种趋势颠覆单一而粗暴的评价体系,提倡创新、冒险、个人主义等价值理念,符合当时美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进而得到推广和流行。
因此,极限运动的城市化也就不难理解。
而尽管脱离日常场景的野外山河更容易让参与者得到非同寻常的体验和感官刺激,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极限运动的普及化,成长于城市的新一代对城市的认同逐渐加深,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城市作为自我表达和体验人生的空间工具。
在城市极限运动兴起之前,由于考量到便利性、熟悉性、经济条件等等原因,不少年轻人习惯在家庭附近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动。街头篮球,街头舞蹈等街头运动在平民区青少年中开始风靡,并和移民的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街头文化,强调反传统、反权威和自我表达。接下来,很自然地,那些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城市有所感受和迷恋的年轻人,开始把表达个性的极限运动从野外带入城市。
城市极限运动与冒险运动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开始兴起,从非主流的小众活动发展到在多国有着各种各样的爱好者协会与赛事。1990年代初,极限运动传入中国,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参与人数与日俱增,其发展速度远远高出了同时 期其它运动项目的发展速度。这种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的城市化风潮。城市场景完美地映衬了极限运动的核心精神,甚至比乡野场景进一步体现了“运动的自由”。
安徽合肥举办的一场国际跑酷大赛
以最流行的城市极限运动之一即跑酷为例。“跑酷”一词源自法文的“parcour”,是“超越障碍训练场”的意思,由两位巴黎郊区的青年大卫·贝尔和塞巴斯蒂安·福坎创立,其核心理念是:在城市中尽情使用本身的力量穿越障碍物,到达目的地。运动由此变得更加自由自在起来,高楼、栏杆、街道,甚至是废弃的房屋都变成了运动场的一部分。
大卫·贝尔表示:“当我在奔跑时,我已决定了一个目的地,并且告诉自己,我要到那里,我要直接到那里,我要迅速到那里,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我一直以来都是《冒失鬼》和《蜘蛛侠》以及其他漫画和动作片中超人类角色的发烧友。我崇拜所有优秀的勇士,和所有自由运动的人。”跑酷文化崇尚的非规则性、自我挑战和个人英雄主义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新型的城市极限运动比之前流行的野外极限运动更无拘无束:以往的不少野外极限运动大多因为自然条件险峻而需要器材的辅助,花费交通成本和大量业余时间,不论是滑翔伞,还是冲浪,抑或是野外攀岩等等,都是“富人的游戏”。而以跑酷为代表的城市极限运动则利用一切唾手可得的身边资源,将随处可见的公共空间看成是健身场所,不需要太大金钱投入,不太受器材限制。像跑酷这样的运动甚至不需要专门抽出运动时间,可以自然地在去另一个目的地时完成,真正体现了极限运动中自由精神。由此,城市的孩子们在熟悉的空间里既达到了运动身体和获得刺激的目的,也完成了人生体验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身体征服城市 运动与公共空间的再定义
城市极限运动的“自由”,不仅仅在于规则与资源上的随性。如果观察近几年热播的城市极限运动视频,不难发现,在有名的街区/建筑或者地标性城市场景中进行极限运动,往往更受欢迎。尤其是像吴咏宁这样的高空挑战者最希望攀爬的建筑,往往是当地最高大或者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在高空挑战相关的网站上,也会有一些关于某位爱好者登上不同高度名建筑的记录展示。这些爱好者们就像野外登山队挑战各大洲高峰一样挑战着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物。极限运动爱好者们似乎用身体“征服”了这些地标,并且通过照片、视频等记录方式在媒体上重新定义了著名地点,把它们变成了自己丰功伟绩的象征。直到现在,不少极限爱好者们依旧在孜孜不倦地挑战那些还没有被征服过的“地点清单”。如此看来,这种新兴的运动和在古代人在某片土地插上旗帜宣告领地的行为异曲同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城市空间,甚至城市空间中展现出的权力结构在这种身体征服的过程中被或多或少地挑战与解构了。
自古以来,城市空间的意义和功能都能体现出明确的权力特征和规则。正如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所说,“空间不过是社会与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城市的地理格局往往具有鲜明的区域划分和特定功能:娱乐、消费、生产、教育的不同空间被赋予了不同特征——例如政府的建筑具有威严性,森严的围墙和大门造成距离感和敬畏感;金融中心的建筑则往往兼具现代感和高级感,强调经济地位的优越性;休闲广场被营造出一种健康、休闲的氛围,低矮的绿植展现出开阔的感觉……这些感受共同塑造着不同区域的权力结构与人们的认知。同时,城市的核心和边缘、建筑的精美与残破也区隔着经济和阶层的不同。通过各式各样的规则,现代城市空间森严的秩序将人重重桎梏。
高空挑战、跑酷、街道滑板等极限运动则打破了这种空间秩序,消解了城市空间的原本的意义、功能和带给人的感受。在挑战者的眼里,所有的建筑、栏杆、坡道、广场、围墙等等,都只是身体征服的客体,被作为挑战对象重新衡量。这一个建筑和那一个建筑的区别,并不是功能、外观、阶级的区别,而只是高或矮、平缓或是陡峭的区别。在进行极限运动的过程中,城市空间不再是控制和规范身体的限制场所,而是作为让身体释放和表现的场景存在。通过攀爬者充满刺激和趣味的动作展演,高楼大厦从严肃和规范的正式空间变成充满娱乐与快感的新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照片和视频强烈影响着城市极限运动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直播技术兴起之后,依托手机镜头和互联网,个体得以实时作为自媒体,与外界跨越时空沟通、交流。这些来自跳跃、攀爬、疾走视角的城市图景,真切地记录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介入和参与,身体对城市的征服已经被镜头精确捕捉,以往总是隐藏于种种服饰和行为规范的身体,得以裸露或展现自己的特色,各种放肆、刺激的动作打破禁忌,获取到了与庸碌日常不一样的愉悦,身体摇身一变而成为图像和场景的主角。对于那些在屋顶仰望城市天际线的高空挑战爱好者来说,最美丽的画面不仅仅是鳞次栉比的建筑与脚下汹涌的人潮,而是“征服”过后充斥着平等主义和自我体验的城市风景。最终,对于运动者和观看者们来说,因为这样的身体介入体验,城市才变得更有实感,不再只是“他们的城市”,也变成了“我们的城市”。
城市极限运动的异变 标签和商业化
不过,和许多亚文化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一样,在普及和流传的过程中,城市极限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异化,丧失最初的自我性和反抗性,逐步被商业收编。更何况,城市空间的利用与意义再生产,只是在既定的背景下进行表演,很难脱离开社会规训的约束。高空攀爬所选择的地点、街头滑板所用的装扮、跑酷所选择的路线等等,无一不容易落入商业集团所塑造的形象之内,追寻身体自由的行为本身也容易因为其刺激性和新奇性被彻底商品化。
吴咏宁的高空挑战行为就是当代城市极限运动商业化的明确反映。2017年2月10日,吴咏宁第一次尝试发了一条关于高楼极限运动的视频,内容是在10楼边缘玩平衡车。这条视频获得打赏130多元,并伴有网友惊讶与称赞的留言。自此,吴咏宁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经常上传高楼极限运动视频,且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度和收入,楼层高度和动作难度逐渐加大。最后更新的视频中,吴咏宁在高楼外侧扒着楼顶边缘做引体向上,并有单手动作,非常惊险。显然,吴咏宁不是单纯的爱好者,而是把极限运动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的微博名也从“演员吴咏宁”改为“极限-咏宁”。在吴不幸去世后,另一个高空挑战爱好者巴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觉得网络视频害了他,因为有粉丝打赏之类的。”
2013年9月,奥地利“蜘蛛侠”迈克·凯米特
登上长沙一座新建高楼并跳伞着陆
除了直接贩卖刺激之外,城市极限运动更多是依靠酷文化的建立来获取利益。通过制造某种流行与时尚的“酷文化”,这种刺激的运动扮演着划分社会阶层的角色,构建着爱好者个人身份与群体认同。能够接触到这些“新潮”文化的中产阶层,把追逐动感的街头文化变成了获得标签的新指南,使得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
商业传播和消费的巨大影响力从跑酷的流行历史就可见一斑:大卫·贝尔主演的电影《暴力街区》直接影响了跑酷的知名度。之后,一些商家开始不断制造和跑酷相关的个性消费产品或者选择赞助,把自己的品牌和文化链接起来,从而告诉爱好者们:只要消费,你就可以变得很酷。如著名的运动品牌K·SWISS 专门为跑酷者设计了名为 Ariake 的跑鞋,彪马公司慷慨赞助了跑酷电影《企业战士》中跑酷者的服装,一时间引发了不少购买和装备模仿热潮。精致的“装备”和昂贵的潮牌一起,再度给本来充满着人人参与精神的城市极限运动架上了准入门槛。除了贩卖装备之外,还有各类商业竞赛、品牌活动、媒体宣传或明或暗地鼓励大众迷恋城市极限运动,刺激消费和身份塑造。发展到现在,充满叛逆的身体宣言与商业广告已经再难区分,城市极限运动的很大一部分,重新回归到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的领域内。
和其他亚文化不同的是,极限运动存在着很大安全风险,但显然,安全问题并不在商业宣传的范畴内。出于利益上的考量,商家当然希望展现的是敏捷的英雄,而不是惨烈的事故。目前大部分流传甚广的刺激视频中,这些惊心动魄的体验都是有惊无险,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我也可以”的错觉。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城市极限运动还没有明确和详细的规范与限制,在某些城市,极限运动可能是违法行为,而在极限运动较为流行的国家中,也没有专业协会,只有民间自发的兴趣爱好团体,如“某地区跑酷爱好者协会”等等。安全措施上,除了高楼跑步(从高楼顶上沿着墙壁跑到地面)这样的运动有比较结实的安全绳等措施以外,大部分城市极限运动并没有特别专业的设备以保障运动者的安全。对于像吴咏宁一样为了获得收入而参与这项运动的,并不富裕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残酷。在彰显自我价值和被商业挟裹的过程中安全行走,也许是一个比行走于高楼之上更难的命题。
本文转载自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解放空间还是卖命揾食?城市极限运动的前世今生
声明: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禹唐体育原创文章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转载/合作请加禹唐微信小助手,微信号:yutangxzs